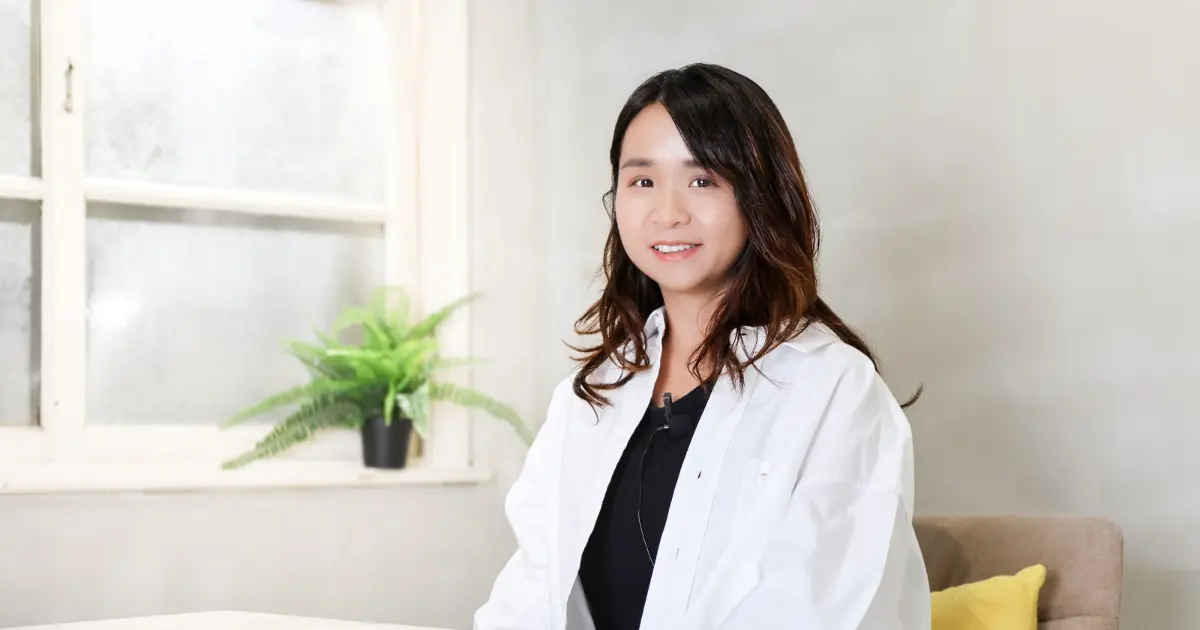在臺灣,許多失能、失語的孩子,他們能聽、能理解,卻無法開口說話,導致他們的需求長期被忽視。2016 年賴姵妏透過朋友的介紹加入了「Sense 森思眼動」(後簡稱森思),一家致力讓科技成為這些孩子與世界對話橋梁的公司,賴姵妏也從此走進了這個亟待發聲的群體中。
2019 年,賴姵妏與夥伴共同創辦了「目目非營利 MUVE NPO」,運用森思的眼動科技解決身障者的溝通障礙,並積極推動身障平權,提升社會對他們基本生活權益的重視。
儘管賴姵妏並非特殊教育體制出身,卻用「聽懂需求、找到資源、把專業接上專業」的方式,將技術與現場一一接軌,即使過程沒有捷徑,但步步都朝同一個方向前進,讓無法言語的重度身障者能用自己的方式與世界連結,而她所做的,不僅僅是推廣輔具,更是打造一條完整的教育與陪伴之路。
飛越制度高牆,為沉默的世界找到出口

起初,森思並未把眼動技術鎖定在身障者,真正扭轉路徑的,是找到市場上沒有人做卻一定要有的剛性需求。臺灣當時缺少為身障者量身打造的繁體中文眼動介面,以及注音打字系統,賴姵妏看見的不只是商機,而是被延宕的身障者權利。
只不過有了技術,不等於打通道路,她很快就撞上制度的門檻,許多人在輔具補助評估上卡關,「有一些縣市的評估人員會認為一定要會使用眼控打字,才能叫做電腦輔具。」但反觀現實,要三、五歲的孩子使用眼控打字、操作眼控滑鼠,門檻高得無法真正落實於需要的家庭。於是她意識到,如果要讓技術接觸到真正需要的人,就必須改變入口,把推動產品轉為打造服務路徑。
從研發深入教育,打造技術與服務的雙引擎
目目非營利的誕生,其實是為了將輔具轉化成教育,並確保有可持續的資源與專門的人力。由於公司沒有辦法募公益款、也無法開捐款收據與申請勸募字號,她與夥伴因而成立這個組織,專責專案募資與課程執行。森思持續在技術上的研發,目目非營利則負責課程執行與師資培育,彼此相依、互為前後端,這樣的分工並不是教條,而是讓每段工作都能持續的深化下去。

再更進一步地,目目非營利把現場需求回饋給研發端,例如與治療師配合,了解需要哪種視知覺遊戲、眼動繪畫軟體,互動繪本如何設計等等;森思則持續優化軟、硬體,讓教學情境更順手。當技術端願意為教育調整、教育端願意清楚說出需求,技術不再只是工具,而是能真正銜接資源與需求。
只不過在初期,新、舊兩個組織難免業務重疊,2019 年,兩邊同時爭取政府或計畫性資源來支撐營運,一邊投入研發或服務創新,一邊尋找適合目目非營利的補助,只要能讓服務延續,只要其中一方先拿到資源,就由那一端先行推動。這樣來回摸索、分配心力的過程雖然費力,但在她心裡,卻是逐步把路走實。
疫情衝擊下的逆勢轉捩,多了被看見的可能

2021 年臺灣疫情肆虐,卻成了目目非營利走向穩定的轉捩點。募資穩定了,資金得以投入長期的師資培訓與區域拓點。過去僅有北部老師,服務的範圍比較局限,尤其花東地區一個月頂多只能跑一次,但隨著他們積極尋找各種管道、申請補助,並在北、中、南、東舉辦一場又一場培訓說明會,到各地尋找師資,困境才逐漸鬆動。而目目非營利的制度、教材與督導機制,在每一次的微調中逐漸成形,服務也開始具備可複製與規模化的條件。
雖然疫情期間,他們嘗試線上課程時遇到困難,許多孩子肌肉張力高低不均,需要老師即時輔助擺位,無法在第一時間調整。但社群的粉絲也大幅增加,先前累積的個案故事也在那段時間開始被更多人看見。
專業培訓與跨域合作,補足眼動教育的最後一哩路
目目非營利透過一對一客製化的課程,幫助重度身障者使用眼動輔具,但這對於身障者與照顧者來說,非常需要穩定的關係與熟悉度。起初,他們曾廣招跨域伙伴,如特教老師、治療師、社工、居服員等,後來發現若不夠熟悉重度個案的身體狀態,孩子與家長的安全感會下滑,導致課程難以推進。
於是,他們重新擬定,將目光鎖定擁有特教或治療師背景的師資,並將培訓期拉長至六個月,前期培訓、觀課、試教、督導遠端或實體輔導,通關後才能開始一對一接案。

改走重質不重量的方向,也意味著無法擴張太快。有些縣市與偏鄉出現師資缺口,有的地區交通來回得花二、三個小時、有些則受限於體制與資訊落差,但目目教學團隊一路上邊走邊播種,持續培訓、與輔具中心及早療單位合作,把入校教學變成讓老師看見孩子轉變的第一現場,讓需求自己長出網絡。
一堂眼動課程大約歷時一小時,為讓孩子們能穩定且有效完成,他們得不斷地調整,甚至將教室拉到戶外,例如帶他們到超商、麥當勞等,讓他們表達自己想要的、想吃的,讓孩子們在生活中增加溝通的動機。
同時,也讓社會大眾理解這群孩子是可以溝通的。賴姵妏分享,有位家長忙完回到客廳,發現電腦上出現孩子自己用圖卡選出的句子:「我想要吃蛋糕」,一句普通的願望,足以把一個家的日常澈底改寫。
從合作授權到自有 IP,目目非營利用眼睛打開全齡的選擇權
為了穩定孩子的注意力,目目非營利曾與文化部、統一超商合作推動「眼動設計工作坊」與《OPEN! 家族旅遊》合作,把熟悉的角色納入視知覺遊戲之中;另一方面他們也打造自有 IP「阿目」眼動童書,讓孩子透過注視觸發情節,這些故事不只好玩,還有深意。市面繪本多半需要大人朗讀、翻頁,重度身障孩童往往只能被動聽故事,眼動童書則反過來,讓孩子成為情節的推動者,並且可以主動去探索。

而對青年族群,目目非營利把課程延伸為線上職能工作坊。眼動老師預錄如何以眼控滑鼠操作 Photoshop、Illustrator、Premiere 等軟體的步驟,從去背到排版、從履歷自介到作品集產出,循序建立工作技能。有些青年甚至開設 YouTube 頻道、設計 LINE 貼圖,用眼睛完成數位創作,為居家就業打開新的想像。
成人的需求更為客製,例如因為中風導致失能、失語的長輩設計輔具,讓他們能夠透過圖卡精準表達哪裡不舒服、學會眼控追球賽或看股市,或者回到真正想做的休閒活動。
提升主動性與生活品質,就是這些課程的最大目的。對賴姵妏來說,她的角色不是定義人生的價值,而是讓身障者也有選擇的權利。
從校園開始的制度化推動,把眼動素養向前扎根
只不過要讓更多家庭接觸眼動課程,僅靠社群與口碑還不夠,必須走進體制內。目目教學團隊與師培院系合作開設講座與參訪,希望讓從業人員在求學階段就能建立眼動素養與實作經驗,而非等進了學校、遇到個案再來找資源。

更長遠的構想,是把「眼動老師」納入校內專職配置,像巡迴治療師一樣服務不同據點,讓師生比與時間表成為可以解的行政題。雖然現實依舊龐雜,也並非單一組織能解決,但當越來越多學校願意開門、越來越多老師願意旁聽課程,制度的轉向就會從一間教室、一個時段,慢慢向外擴散。
為了縮短等候與媒合時間,目目非營利在北部成立第一個實體眼動教室,從烹飪課到繪本共讀,讓老師有更多教學方式可以發揮,也讓家長願意把孩子帶來,換取更穩定的學習關係。而這個據點,是賴姵妏心中「眼動學校」的雛形。她希望目目非營利在五年內可以於北、中、南設立據點,更長遠的願景,是把據點從教室拓展成親子館,讓重度身障者的孩子們,也可以享有自己的遊樂園。
將倡議化作種子,讓無聲者的力量也能長成大樹
今(2025)年 10 月,賴姵妏將第二次擔任社會企業世界論壇(SEWF)的講師,這次的主題為融合教育與共融社會,不只要讓大眾認識眼動技術,更希望能夠幫助大家了解,這個議題與每一個人的關聯。
她說:「如果這個社會缺少了輔助不同族群的方式跟工具,那有障礙的應該是這個社會而不是人。」這不是口號,而是賴姵妏一路上秉持著的信念。
她明白,倡議沒有立竿見影的成果,但每一場展覽、每一個廣播節目的邀請、每一次的媒體採訪,對她來說都是一顆小小的種子,而她不斷在做的,就是持續把種子散播下去,讓它們各自找到土壤,安心地長出嫩芽,成長為大樹,讓每一位重度身障者,都有平等發聲的機會跟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