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屏東三地門鄉「青山(Cavak)」部落的排灣族音樂創作者桑梅絹,她的族名:Seredaw,象徵著「渲染」的意義。自幼,母親就教導她習唱古調,看著部落傳統文化逐漸式微,她毅然扛起傳承的重責,長年在部落教唱。2018 年,她以專輯《渲染》榮獲第 29 屆金曲獎最佳原住民歌手,隔年再度以《記憶中的搖籃》入圍第 30 屆最佳原住民歌手。多年來,她在部落開設教室,教婦女和孩子唱古調,並帶著音樂走向世界。
她說,音樂是她與祖先對話的方式,也是她回應這片土地和世界的橋樑。
從搖籃曲開始的音樂養成

桑梅絹的童年,始終伴隨著古調與母語。她回憶道,母親是一位部落公認的「吟唱者」,擅長在重要祭典、婚禮或部落大事中擔任主音,吟唱傳統的祭歌與古調。母親在日常生活中,會在睡前為她唱搖籃曲,或帶她拜訪部落長輩,向老人家學習不同場合的歌謠。這種浸潤式的成長環境,使她從小便能親近歌唱,從習慣傾聽到自然而然地開口吟唱。
她的家是少數仍保持全族語環境的家庭之一。由於父母年紀較長,受的是日本教育,家裡只講族語,讓她自小養成純熟而深厚的母語能力。父親雖然不是歌者,但最喜歡與她談論部落遷徙的歷史,桑梅絹在很小的年紀就明白自己的族人是如何從遙遠的地方遷徙到青山部落,經歷了哪些考驗才安身立命。她形容這段學習如同「拿到一張身分證」,因為唯有知道自己來自何方,才真正明白自己是誰。

在青山部落,吟唱者不只是音樂家,更是文化記憶的守護人。當頭目家族有事、部落舉辦祭典、或新人迎娶時,吟唱者的歌聲承載著祝福、祈禱與歷史。桑梅絹的姨婆曾是部落重要的吟唱者,母親繼承這份責任,而如今,她也走上同樣的道路。這條路並不只是藝術表演,而是一種身分與使命的傳承。
除了音樂的天賦與文化根基,桑梅絹的生命故事還有一份特別的色彩。她的家族是祭師後代,擁有對環境特別敏感的體質。雖然她因信仰基督教而未繼承祭師職位,但在重要場合,如劇場開演或到陌生地方時,她依然會以傳統儀式祈福,將祖先的智慧與庇佑延續在自己的生命與舞臺上。
從語言壓迫到文化自覺的成長歷程
然而,童年的記憶並非全然無憂。她曾在學校因說母語被懲罰,被要求在椰子樹下向「國語」道歉。「當時我無法理解,為什麼講母語需要道歉?但可能自己生性樂觀,常過了就忘。」這段經歷雖令人不解,卻未能動搖她對母語與文化的認同,因為在家中,父母始終鼓勵她說族語,認識自己的文化。
國中時期,她進入位於高樹鄉的學校,就讀於多元族群混合的環境中;高中則在屏東市的民生家商就讀幼保科,因喜愛小朋友而立志成為幼教老師。她 17 歲便開始打工,做過餐廳服務生、總機接線員,也曾在幼兒園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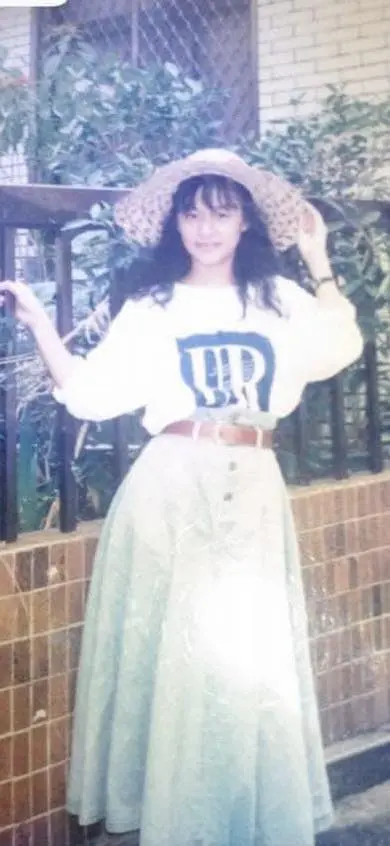
然而,音樂的種子就像某個無形的存在,悄然在她心裡萌芽。小時候的部落晚會和節慶,總有長輩鼓勵她站上舞臺唱歌、跳舞,那種被期待的光芒,讓她自小就想成為「歌星」。雖然家人曾擔心演藝環境的複雜而勸阻,但音樂從未真正離開過她。
從導覽員到開設部落古調教室 以歌聲守護部落記憶
2012 年,她爭取到原住民族委員會的「駐村藝術家」計畫,連續三屆獲選,得以在部落開設教室,免費教導婦女與孩子們學唱古調。這段時間,她每天晚上都開課,從不強制收費,唯一的條件是「來上課就要專心」。
在教學過程中,她不只傳授旋律與歌詞,更讓孩子們理解古調背後的故事——有些歌記錄著部落的遷徙史,有些則訴說家族的記憶。為了讓不會讀羅馬拼音的孩子也能學唱,她用注音符號輔助,一句一句耐心教唱。她笑說,最小的學生才三歲,而自己的女兒,就是在耳濡目染中成了她的「助教」。

在教學的歲月裡,桑梅絹見證了許多孩子的成長。儘管有些父母擔心影響課業而反對孩子學唱古調,但也有家長體諒她的辛勞,主動準備點心支持。她認為,語言與文化同樣重要,「讀書」與「傳統」可以並行,而古調正是讓孩子認識自己身分的重要途徑。
打破傳統禁忌 成為第一位傳唱〈報戰功〉的女性
除了日常的教學,桑梅絹承接部落的〈報戰功〉吟唱更是一段珍貴的際遇。這首戰功歌原本專屬男性吟唱,歌詞內容意指男人上山狩獵後,用來宣示獵區界限,展現勇士榮耀,甚至帶有嘲諷懶惰、不擅打獵者的意味。當部落最後一位男性吟唱者因年老而無法繼續傳唱時,他親自指名將這份文化交給桑梅絹。起初,她擔心以女性身分演唱會遭非議,甚至被丟東西,但老人家的話讓她動容:「如果你不唱,等我走了,就沒有人會了。」最終,她獲得頭目的同意,成為部落唯一被允許公開演唱〈報戰功〉的女性。

第一次在祭典上報信並演唱〈報戰功〉時,她從臺上哭著走下來。那不僅是因為自己打破了傳統,更因為她深切感受到文化流失的現實與沉重。她說:「看著族人拿著槍,卻不會唱屬於自己的戰功歌,也因文化在殖民過程中不斷流失,我們還能如何稱自己是勇士?」對她而言,這不只是歌曲的延續,更是對族人失落文化的叩問與提醒。
從古調改編到全創作 用母語唱出當代排灣之聲
成為歌手前,她曾擔任文化導覽員,導覽過程中,為遊客清唱古調以填補講解的空檔,意外引起熱烈反應。她笑說:「唱歌原來也是可以做的工作。」桑梅絹雖然是部落裡重要的吟唱者,卻不滿足於僅僅保存古調,而是嘗試用創作,使傳統音樂在當代重生。從 2017 年推出首張個人專輯《渲染》、2018 年發表第二張作品《記憶中的搖籃》,到 2023 年的第三張專輯《夢境》,記錄了她從文化承繼者蛻變為創作者的里程碑。
《渲染》專輯以古調改編為主,融入自身的生命故事。希望能打破外界對古調「難懂、遙遠」的刻板印象,讓旋律保留原味,同時改變唱法與詮釋方式,貼近現代人的感受。她強調:「每個世代有不同的生活經驗,唱法自然不同。」

另一首〈選擇〉則源自百年古調,原本是一位老人家坐在石板屋上挑女婿時的情歌,前半溫柔吟唱,後半帶著失落的哭聲。桑梅絹將其轉化為自己的故事——15 歲時面對部落傳統的「提親」壓力,她在歌中唱出對早婚的不解與掙扎:「你們一直在挑,但我也在挑,為什麼一定要現在?」她保留古調旋律,將歌詞改以排灣族語文言寫成,賦予傳統旋律嶄新的情感指向,也是將生命片段直接轉化為音樂的真誠告白。
跨越國界的音樂交流與文化情誼
不同於過往以古調或改編為主的作品,第三張專輯《夢境》是桑梅絹的自我宣言。她直言,古調屬於祖先的聲音,而《夢境》要留下的是屬於當代的桑梅絹,讓後代透過她的歌聲認識當代的排灣族生活與情感。專輯曲風多元,融入爵士、古典等元素,展現她跨越傳統與現代的音樂視野。
同名曲〈夢境〉源於她首次前往澳洲原住民地區駐村時的真實經歷。抵達當地後,她參與祈福儀式,當晚夢見一位老人站在清澈的溪水中央對她微笑。部落長者為她解夢:「你是被祝福的,無論走到哪裡,主都與你同在。」這段經歷讓她深感平安,也成為創作靈感。
另一首〈白妮〉則是她對澳洲原住民夥伴的致敬。多年跨國共創的合作中,對方為她取了「Baini」這個象徵大地之母的名字,讚賞她溫暖、包容的特質。雖語言不同,她們卻能在音樂與藝術中找到深厚連結。歌曲以感謝為主題,傳達「跨越語言與文化,我們依然可以成為家人」的情誼。

多年來,桑梅絹帶著音樂走訪西班牙、日本、韓國及多個南島國家。她回憶在南太平洋的離島演出時,觀眾看到她的排灣族圖騰與聽到其歌聲,第一句話便是:「臺灣是我的母親之島。」那份跨越語言的共鳴,讓她更加堅信音樂的力量,「只要有歌聲與呼吸,就能被理解與接納。」
如今,桑梅絹仍在舞臺與部落教室之間來回穿梭,既是歌手,也是文化的傳遞者。她用一首首歌,讓排灣族的歷史與精神在時代的洪流中不被淹沒。對她而言,每一次的吟唱,都是與祖先的對話,也是對後代的承諾——文化的火種,必須一直唱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