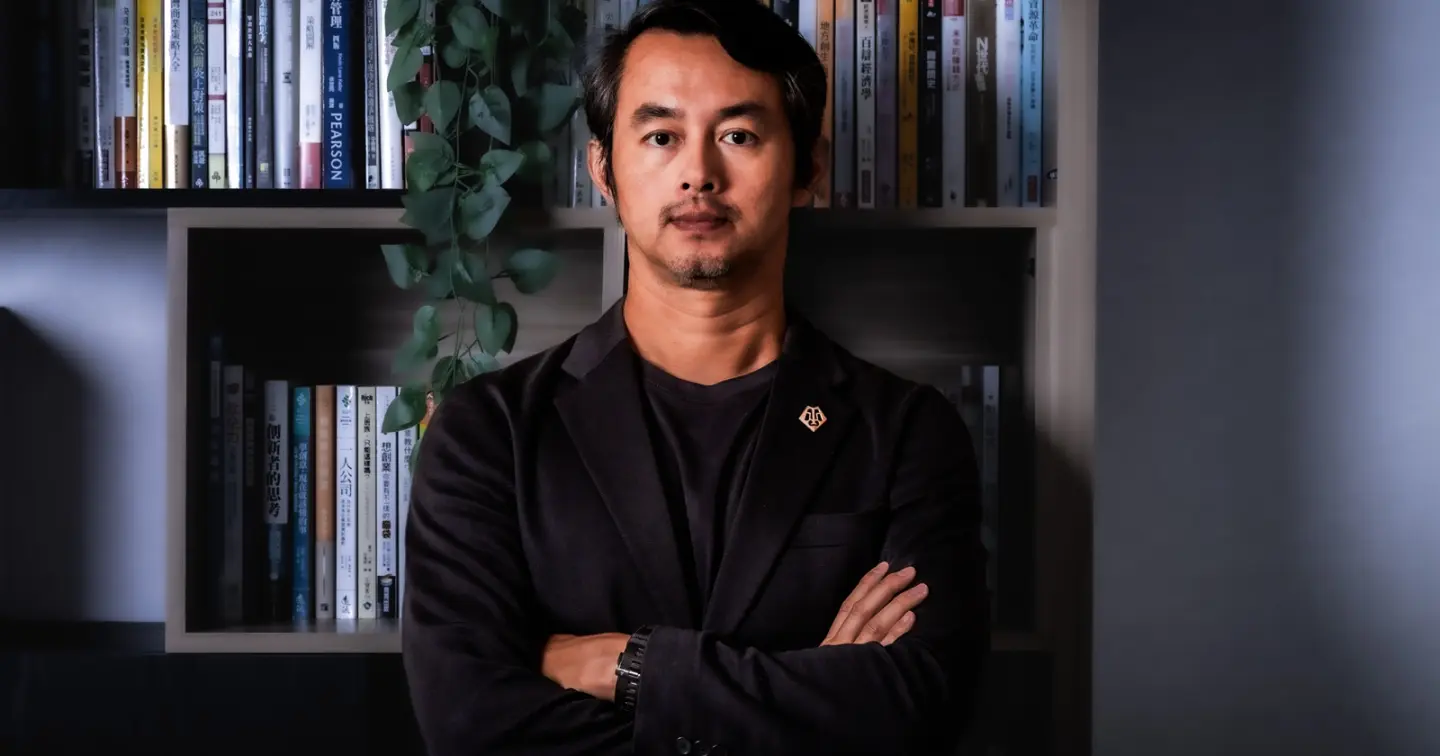從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到律師、從男性的「陳漢章」到如今被親友喚作「樂樂」的跨性別女性,他用 40 年的時間學會與自己和解。赴日研究的一年,讓他首次以女性的樣貌生活,也意識到「快樂可以如此簡單」。返臺後,勇敢解放多年的壓抑,穿上女裝、接受荷爾蒙與聲帶治療,成為體制中少見以真實樣貌出現在公眾面前的跨性別司法官。如今,陳樂樂卸下公職轉任律師,將時間留給家人,也成為許多跨性別者的心靈支撐。
叛逆少年到司法官:為自己第一次用力讀書
「我小學就不愛念書,讀書都是為了別人。」陳樂樂說。高中聯考意外考得不錯,順利上了大學:「我大學幾乎不去上課,整天打電動、唱歌、夜生活。要說我在大學有念書,絕對是騙人的。」他笑著說自己的畢業成績甚至是「全班倒數第三」。
真正的改變,是在踏入社會後,做過雜誌編輯,發現自己並不適合出版業的作息與薪資結構。「朋友找我一起準備國考,還說:『我們考上律師後一起開事務所,就能繼續一起玩。』那是我第一次為自己想像未來,也第一次真正認真念書。」他坦承:「其實我也不是不會讀書,只是過去從未為自己讀。」
順利通過考試後,投入司法體系,成為檢察官,自此走上與年少時截然不同的軌道:嚴謹、秩序、節奏分秒必爭。然而,內心裡有另一個聲音,並未因此沉寂。
壓抑 40 年的慾望在日本獲得釋放

「國小中年級,我就很清楚自己不一樣。」那不是一夕之間的覺醒,而是一路被訓練成「別人眼中的正常男生」。國中開始,他會偷買女生的衣服,在房裡穿上,體會「終於協調」的放鬆。「我會嫉妒女生,為什麼她們可以那樣漂亮、留長髮、穿裙子,而我卻不行?」
成長過程,陳樂樂學會偽裝,融入團體,避免被貼標籤,懂得在男性群體裡「活得很好」。他說:「我很在意朋友,知道只要露出一點跡象,就可能交不到朋友。」這份渴望被長期封存,只有在極少數的私人時刻,才能短暫透氣。
直到 40 歲赴日進行一年研究,心境有了改變。「在國外的那一年,我 24 小時都能照著自己喜歡的樣子生活,只有與教授會面時會『扮回男裝』。」那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定感,不再感到焦慮,世界變得柔軟。「我這時才知道,原來每天都可以很快樂。」
快樂如此真切,以至於回到臺灣,再也壓制不住慾望。「以前我只有一天的十分之一能做自己,回來臺灣後,要再回到那個比例,我做不到。」他開始求診、諮商。陳樂樂沒有做性別重置手術,但經過醫生評估後,選擇使用荷爾蒙治療,並接受聲帶手術,讓外表與聲音更接近心中理想的樣貌。「我不是為了迎合誰的定義,我只是想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自由,是誠實地活出自己:陳樂樂的性別哲學

談到對性別與自我認同的理解,陳樂樂認為「性別認同」與「性傾向」是兩件不同的事。前者是「你認為自己是誰」,你可以認同自己是男性、女性、非二元或介於之間;後者則是「你被誰吸引」,無論是喜歡男性、女性或其他身分,都是獨立存在的選項。「這兩者可以自由組合,就像生理男女之中也有同性戀一樣,跨性別者裡自然也會有同性戀與異性戀。」他解釋。
陳樂樂認為自己屬於「跨性別的同性戀」。雖然心理上傾向女性,也希望自己能以女性的樣貌生活,但情感上依然被女性吸引。他曾一度渴望澈底「成為女人」,直到某一刻才明白,那樣的執著讓他越來越不快樂。「當你不停糾結自己到底是男還是女時,其實就被他人的標準綁住。」他認為,即使做了所有改變,仍會有人不認同、質疑甚至否定,「那為什麼要讓別人的眼光決定我的存在方式?」
真正的自由並不是透過手術、證件或外貌去證明什麼,而是學會放下迎合的焦慮,誠實地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我後來明白,我的課題不是如何變成女人,而是如何成為我喜歡的自己。」他的語氣平靜且堅定,「當你允許自己這樣生活,你會發現,快樂其實很單純。」
從「急」到「柔」:做自己後,專業更順利

重返職場後,他以更女性化的樣貌出現在單位與法庭,外界最關心的,是這樣的改變會不會帶來衝突與阻力?但他的經驗意外地平順。「同事和長官其實都很保護我。」陳樂樂說,曾有資深長官透過主管轉述「頭髮太長」,希望他能剪短,主管當場回應:「留長髮是他的權利。」成了他職涯裡一段被接住的記憶。
當做回自己,陳樂樂注意到自己偵辦案件的風格也變得不同。「以前我很急躁,一進來就問、就攻堅。」如今,他會先遞水、先讓對方坐好,「你想講就講,不想講也沒關係。」溫柔降低了防衛,訊問反而更有效率。
「你越柔軟,對方越願意說出平常不會講的事。效率、情緒與掌握度,反而更好。」他說,這不是「討好」,而是更懂得尊重「人」的差異性。
婚姻的四年痛:從伴侶到家人

提及婚姻經營,陳樂樂表示,太太發現他喜歡穿女裝時,只把它視為一種「興趣」,然而在他做出「每天都做自己」的決定後,兩人進入漫長且艱難的磨合期。「妻子以為她愛的人會一直是『那個樣子』,要她改變對象的性別圖像,太難了。」兩人的關係因此陷入僵局近四年,陳樂樂只能試著用「對她更好」來彌補對方的不安,卻發現那不是同一件事。
轉機來自兩年前,媒體報導帶來大量關注與邀約,太太把心力轉向社群經營、寫作、活動,情緒得以轉移。兩人也終於能「理性對談」。他們的婚姻不再是情侶關係的延伸,更像是親人、夥伴、共同經營家庭的人,以對孩子的關愛為優先考量。「只要她快樂,我什麼都願意給。」陳樂樂與妻子的愛情形式不同了,但愛的重量並沒有改變。
父職 × 性別教育:一個愛漂亮的爸爸

七歲的兒子會怎麼看待自己的父親跟其他同學父親的不同?陳樂樂說,對兒子而言,爸爸一直都是他現在的樣子,沒有「過去式」需要適應。面對孩子同學的好奇,陳樂樂有一套簡單而溫暖的說法。「世界上的爸爸很多種,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樣貌各異。爸爸真正的意義不是長什麼樣子,而是:我很愛你。所以我是你的爸爸。」
他也教導孩子要保護自己,不必向所有人解釋一切。但兒子有時會熱情過頭,會想把「漂亮的爸爸」介紹給全班認識。「我會盡量避免把大人的世界、網路的風險帶進校園,但到目前為止,家長與同學都很友善。」他說,當大人懂得尊重彼此的不同,孩子也會把你視為「眾多大人中的一位」。
今(2025)年,他卸下檢察官職務,轉任律師:「我想要更多陪伴家人的時間。」檢察官身分有諸多限制:交往對象的申報、公開活動的規範、與社群互動的邊界等。高度曝光與龐大案件數,讓他感覺自己始終站在被放大檢視的鏡頭底下。「我想把節奏放鬆一點。」陳樂樂理想的一天,是自然醒、運動、吃飯、處理案件,再回家陪孩子寫功課。
真正的勇氣,不是決裂,而是仍願意與世界相連

談起對年輕跨性別者的建議,陳樂樂沉吟良久,格外謹慎。他提到,自己不輕易給予建議,因為每個人的生命經驗與環境都不同,但若一定要說,他最想提醒的是:「不要主動切斷你的人際關係。」
他觀察到不少年輕跨性別者在自我探索的過程中,會急著與過去的身分劃清界線,甚至刻意「切斷過去」。但這樣的斷裂往往讓他們在新的環境中更難建立對人的信任,也更容易陷入孤立與焦慮。「沒有支持系統的人,生活是很辛苦的,」他語重心長地說,「孤單久了,內心會生病、變得憂鬱,甚至可能會自我毀滅。」
若是面對家人的不諒解,陳樂樂呼籲要保留善意。「很多家長的反應只是情緒性的,不一定是真的要斷絕關係。」他舉例,若被趕出家門,也可以用平和的語氣表達:「我理解你的擔心,我過得好,隨時都能回家。」時間久了,父母往往會因為看見孩子的穩定成長而慢慢改變。
陳樂樂認為,真正的勇氣不是與世界決裂,而是仍願意與世界保持連結。「每個人走出來的方式不同,但那顆願意維繫關係、繼續相信愛的心,才是讓人得以存活的力量。」
在法律的世界裡,她學會秩序與界線;在自我的旅程裡,她學會溫柔與堅定。離開檢察官、成為律師之後,陳樂樂把時間還給了自己與家人,而她留下的,可能是一種更難卻也更重要的專業示範:當一個人被允許做自己,他/她的專業與內在,往往也會更好也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