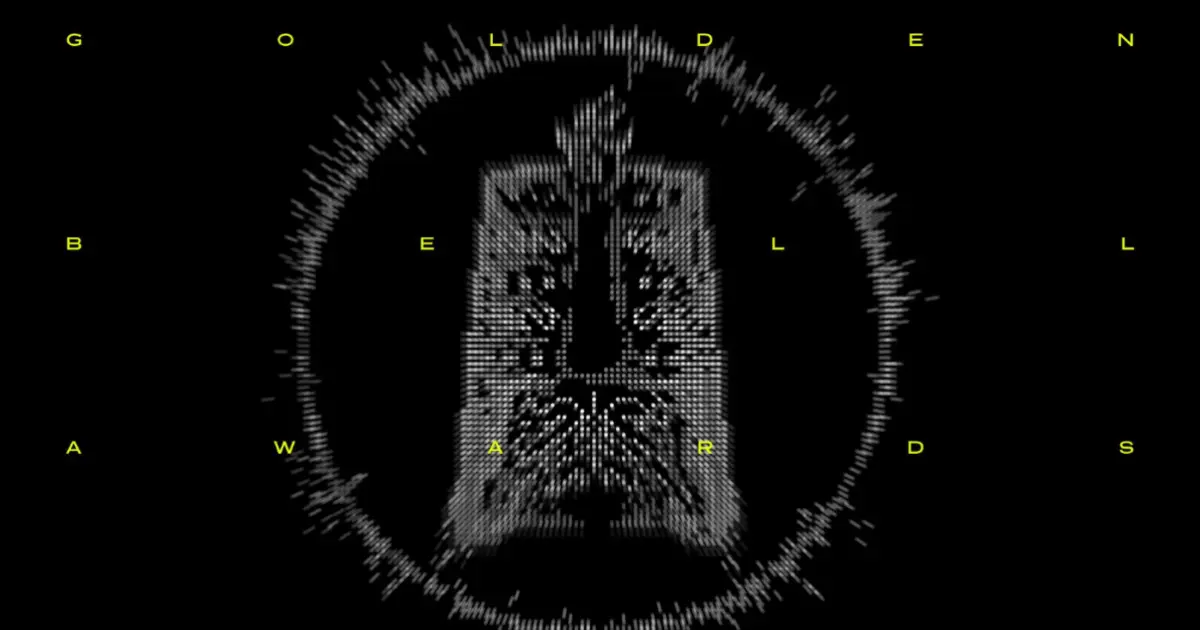第 60 屆金鐘獎揭曉入圍名單,《星空下的黑潮島嶼》以 16 項大獎提名成為矚目焦點。導演王傳宗坦言,榮耀背後更重要的,是讓觀眾看見歷史記憶與人性光影。從《我的阿嬤是太空人》探觸安寧照護,到新作將白色恐怖化為群像書寫,他始終以溫潤的手法,為社會上最尖銳的課題尋找一條能被理解的敘事之路。對王傳宗而言,影像是責任,也是他與時代對話的方式。
傳說火燒島(綠島舊名)上的象鼻岩是「鬼門關」,黑暗中有去無回,但只要有一點光,就能在黑夜裡走得更遠。
《星空下的黑潮島嶼》以 1950 年代綠島為背景。韓戰爆發後,島上成為思想改造之地;被稱為「新生」的政治犯來自四方,農民、學生、教師、藝術家與醫師並置,操客語、日語、台語、國語的島嶼混聲在高壓監控與物資匱乏中交織。
本劇的靈感源於一張歷史照片:幾位臺灣年輕醫師與軍醫合影,政治犯身分的醫師竟站在畫面中央。王傳宗說,自己長年關注白色恐怖,卻從未在教科書或影視作品看見「醫者群像在監所中重建醫療系統」的故事。
2018 年讀到米果於《獨立評論》的文章——〈曾經,火燒島有最強的醫務室〉,確定「應由我們來說這個還沒被說過的故事」。他自受難者顏世鴻自傳《青島東路三號》入手,循線查證人名與事件,登門訪談胡子丹、張常美、蔡焜霖等前輩,將田調化為劇本,2018 年入選公視第一屆劇本孵育計畫,逐步走向拍攝。
在田調碎片中拼組出故事樣貌

團隊在田調中聽見最日常也最關鍵的記憶:「生病就去找『胡啵誒』」。這個「啵誒」即是 professor 的「pro」,影集中鍾富源(王識賢飾)的原型人物胡鑫麟便是由此而來。王傳宗說:「我們透過受難者看病的生活片段,拼湊出醫務室的全貌;那是一個幾近沒有文明的地方,卻能建立起可治腸胃炎、拔牙、割闌尾的醫療系統。」
為復原時代質感,團隊在臺南岸內影視基地大規模搭景,並以約 1,500 顆特效鏡頭重建彼時島上風土與夜空亮度。「我們不做平行時空,而是盡力貼近曾經發生的現場。」在歷史可考與戲劇有效之間,建立跨部門查核機制,醫療場景亦諮詢專業,力求讓專科醫師看了也點頭。
田調之路漫長且繁重,「政府一直在做轉型正義與口述歷史,我們從中獲得很多資料。但真正的功課,是把這些書、檔案與訪談,一字一字讀過,再找出故事線。」團隊將各部會與研究機構保存的口述史一冊冊「翻落書架」,從冗長生命史中擷取與綠島相關的幾頁筆記,再逐一交叉比對。王傳宗也登門訪問胡子丹、張常美、蔡焜霖等前輩,將散落的碎片串連成完整劇情。
在「做對事」之外,還必須「把事做對」。他指出,物理層面的查核——服裝、飲食、帽飾、居住型態與醫療器械——有圖可考,只要花功夫就能準確。更難的是史觀的平衡:「你覺得是控訴,軍方會說是管教;我們做的,是如實呈現處境,讓觀眾自己判讀。」
此外,團隊邀請歷史顧問林傳凱協助史料考證,美術部門一比一復刻場景。在不違背歷史精神的前提下,適度為戲劇服務,例如歷史上新生們的確曾做出礦石收音機,為避免禍及同袍立即砸毀,但戲中保留其存在,成為角色撐過黑夜的心靈依託。「那不是虛構,而是把真實的情感功能,轉化為可見的戲劇道具。」
歷史與影像的雙重考驗

製作過程歷經幾番波折:疫情攪局、剛進入岸內影視基地搭景即遇投資撤資,劇組不得不暫停,直到客家電視台加入,2023 年 3 月重新丈量、復工搭景,前後耗時七年才拍成。
「我們總會問前輩:『希望你的故事被拍出來嗎?』大家都說『很希望,也希望能活到被看見的那天。』」最熟識的受難者前輩蔡焜霖,於 2023 年 9 月 26 日公祭;劇組隔日開鏡。「原想邀請他來現場。這讓我們更確信,影像其實在跟時間賽跑。」
長年浸潤史料,翻轉了王傳宗對白色恐怖的單一路徑想像。「我原以為這是一部訴苦與控訴的史詩;但在口述裡看見更多『既然來了,就讓大家一起好』的精神。醫師治病、老師教字、有人教英文、有人種菜改土、有人蓋醫院與學校。他們不只自救,也扶助了綠島居民。」在資源稀缺、存活仰賴搶奪的環境中,前輩們仍以「品格與風骨」彼此要求,王傳宗說,這正是他最深的感動。
至於片名《星空下的黑潮島嶼》,則將自由與束縛、希望與圍困並置為意象。「星空代表無垠與自由、黑潮是環繞孤島的洋流,也是政治上的無形限制。抬頭望星,你能抵達更遠的地方。」劇組甚至推算出 1951 年前後不同季節的星象亮度與方位,於後期微調鏡頭構圖,使角色視線所見與當時天文相符。「即使觀眾不一定察覺,我們仍想把那個年代『真的會出現的星空』放回畫面,讓時間成為影像的一部分。」
從影評人到導演:故事與議題的雙重視角

王傳宗早年以「金桔粒」筆名寫影評,後轉向導演、編劇,跨越單元劇、影集、紀錄片與音樂錄影帶。大學時,就讀英文系,沉浸美國文學、西方神話與電影文本之間。他笑稱這段學習,除了讓英文能力扎實,更讓他能快速理解國外電影中大量的典故與隱喻。「當別人不懂角色對話裡的神話暗示時,我因為有相關知識,就能看懂。」
研究所轉向新聞學,訓練他在龐雜資訊中挖掘議題,並轉化為可被理解的故事。「新聞所要求我們必須對議題敏銳,能從日常發現隱藏的故事,再加以整理、核實。」這樣的雙重養成,成為他日後拍片的重要基底:既能理解影像語言的隱喻,又能精準觸碰社會現實。
王傳宗真正走入專業影視,與公共電視密不可分。彼時各大電視臺以資本為門檻,唯獨公共電視透過公開徵案給予新人機會。王傳宗回憶:「即便默默無名,只要你的故事大綱過關,就能獲得資金支持,這讓我第一次把企劃轉化為真正的影像。」
這段歷程培養他將「硬議題」轉化為「軟故事」的能力。例如《我的阿嬤是太空人》表面是家庭敘事,實則談的是安寧照顧;《天使的收音機》觸及聽障家庭;《阿弟仔知不知道》則書寫智能不足長者與陽光基金會的故事。「議題很硬,但影像必須溫潤。觀眾是透過情感理解議題,而不是被說教。」
除了公共電視的議題劇,王傳宗也拍過廣告、偶像劇與商業片。他坦言,這些經驗讓他理解市場語言,包括如何跟製作人溝通、如何與觀眾對話。「我知道怎麼灑狗血、怎麼拍浪漫,但我更希望這些技巧最終能回到議題性的作品上。」對他來說,不論走哪條路,最終都會匯流到「找到題材,並以觀眾能理解的方式拍出來」。
教學現場:把種子撒出去

現任崑山科大視訊傳播設計系教授的他,也將片場經驗帶入教學。他常比喻:「教學像是撒下一把肥料或澆下一桶水,你不知道哪顆種子會發芽並長成大樹,但你必須無條件灌溉。」
他回想第一次進片場的震撼,在廢墟般的松山菸廠,看著外國攝影師與燈光師架設機器,重新解構了電影院裡的幻象。「我強迫自己記住那份興奮,所以現在我也希望帶學生去感受。」因此,他曾帶逾 50 位學生進入岸內影視基地,參與美術組實習,從做老家具到道具製作,讓學生在現場體驗兩個多月的拍攝節奏。
「每個學生都是種子,能不能長成大樹無法預測,但我希望至少能給他們養分。」
王傳宗坦言,幾年前經歷過大病,已不再能像年輕時一天拍攝 18 小時。他因此更注重拍片安全。「沒有一個畫面值得拿命換。」他強調,如今帶學生實習,首要規定就是「安全收工」,要學會控制工時,不讓悲劇重演。「美可以再追求,但生命只有一次。」
下一個十年:更大題材,更長時間

談到未來十年的創作方向,他透露,自己正著手一個與「對臺灣影響深遠的外國人」有關的大題目,目前還在田調階段,預計三、四年後才有機會問世,接下來會更專注於需要長時間前置、難度更高的作品。他說:「我希望能留下對社會更深遠的影像記錄。」
從安寧療護、失智照顧,到白色恐怖與無家者處境,王傳宗的作品看似冷峻,卻總帶著溫柔的人性之光。「議題是硬的,但故事是軟的。當觀眾在劇中看到自己、看到他人,那個瞬間就是理解,也是共感。」
正因如此,《星空下的黑潮島嶼》不僅是金鐘 16 項入圍的作品,更是王傳宗創作軌跡的延伸:將艱難歷史與個體命運交織,拍攝成能夠撫觸人心的影像。未來十年,他將繼續走在這條路上,用鏡頭記錄時代、守護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