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顆心可以碎,還有一個夢可以圓,還有一個家可以回……」午後時分,一道渾厚、飽滿而真摯的嗓音照亮了昏暗的錄音室。音樂劇演員張世珮高聲唱著,改編自李安導演同名電影音樂劇《飲食男女》中的代表曲〈還有一顆心可以碎〉。這天下午,她用音樂劇演員獨有的「說故事聲音」,為我們拉開序幕,走進一齣有笑、有淚、有挫折,也有感動的作品——那是一部名為《張世珮的劇場旅程》的動人音樂劇(Musical)。
提到音樂劇,你腦海中浮現出的是哪一段旋律?是《貓》裡淒美哀婉的〈Memory〉,還是《歌劇魅影》驚心動魄的高音二重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如果你認為音樂劇好像不夠親民,那麼迪士尼動畫電影《冰雪奇緣》的國民神曲〈Let it go〉,以及《美女與野獸》的浪漫主題曲〈Beauty and the Beast〉,相信你一定不陌生。
音樂劇早已悄悄滲入大眾的日常,而在百老匯與倫敦西區之外,臺灣也有一群默默耕耘的藝文工作者,用聲音與熱情,灌溉著這片土地上的音樂劇種子,讓它一點一滴地發芽茁壯。張世珮,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為臺灣音樂劇界的女高音,她用聲音訴說角色、點亮舞臺,溫柔照亮了這條不易走的藝術之路。
序幕:意外闖入音樂劇領域 用聲音打開劇場的大門
在四面都是鏡子的教室裡,空氣瀰漫著緊湊的節奏與汗水的氣味,一群人反覆排練走位與舞步,上一秒高聲歌唱,下一秒淚流滿面。這是音樂劇的排練現場,每一位幕前幕後的人都像一顆螺絲釘,緊密咬合、環環相扣,只要少了一人,整齣戲便無法運轉。
「劇場演員和工作人員都是在同一條船上,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讓戲好看!」在劇場耕耘超過 20 年的張世珮這麼說。身為臺灣音樂劇界的靈魂人物之一,以嘹亮動人的歌聲與一絲不苟的專業態度,在這個仍屬小眾的舞臺上,鑿出一道堅毅的光景。
從小熱愛唱歌的她,高中就讀音樂班,大學主修聲樂,求學生涯始終與音樂相伴。擁有著父母與師長口中的「天生好嗓子」,唱起歌來穿透力十足、情感飽滿,彷彿被天使吻過的聲音,讓她順理成章走上聲樂之路。
然而,那份與生俱來的爆發力,逐漸成為身體難以承載的重量。張世珮發現,自己的嗓音固然宏亮,但唱起來常感覺吃力、失衡,難以切實表達內心情感;而面對聲樂舞臺,尤其是傳統歌劇(Opera),也開始感到格格不入,那些以外文演唱、劇情重複的經典作品,雖然已有許多前人留下的教學範本,卻無法滿足她想恣意歌唱的心意。畢業後,她便毅然決定離開聲樂界,轉而加入合唱團,延續對歌唱的熱愛。
2004 年,一通學妹的電話改變了她的人生軌道。當時張世珮正坐在客運上,意外接到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自製音樂劇《天堂邊緣》的「合音天使」演出邀約,沒有名字、沒有角色,甚至沒有一件吸睛的服裝,只有純粹的聲音展現。

「記得第一次看到排練,我淚流滿面,因為那個戲好感人。我從來沒想過音樂劇可以這麼打動人心。」她站在排練場一角,看著臺上演員進進出出,情感濃烈地唱著歌,深受震撼。不同於過去純技巧的聲樂訓練,音樂劇讓她第一次感受到,聲音不只是共鳴與音準,而是一種能觸動人心的語言。而更令她驚喜的,是《天堂邊緣》使用她最熟悉的中文,終於,她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講述屬於舞臺的故事。從那一刻起,張世珮踏入了劇場領域,開啟了她與音樂劇漫長而深刻的同行。
上半場:劇場如人生 激出音域裡的破框之聲
舞臺是一條沒有回頭路的選擇。自從踏進劇場,張世珮就把自己全心投入其中,再難也不喊累,再苦也不退場。
作為音樂劇演員,除了唱歌,跳舞和演戲同樣是必備技能,當時並沒有專門的表演課程可循,只能在一部又一部作品中摸索、淬鍊。「我曾被導演說,我唱歌的時候像企鵝,兩隻手擺在旁邊晃來晃去的。」於是她每天回家對著鏡子練習,推敲每一次呼吸、每一個情緒點,從聲音延伸到身體的表達。但真正讓她頭痛的,其實是跳舞。
「我是出了名的不會跳舞,現在都挑不用舞蹈的角色。」她如此自嘲。但只要角色需要,仍會一個動作、一個節拍地苦練,光是記舞步就要練上一個月,「不會就練到會。」是她給自己的規則。
就這樣,張世珮用一次次的實踐,在劇場中站穩了腳步。直到被觀眾稱讚「演得好」,不再只是「唱得好」時,才終於能放心地說:「我是個音樂劇演員。」在這條不斷突破自我的道路上,遇見了真正能激發她表演潛能的角色,是天作之合劇團音樂劇《飲食男女》中的長女朱家珍。那是一位壓抑自我、過度承擔責任的角色,和張世珮本人開朗、直率的性格截然不同。如此的反差,對她而言是極大的挑戰。

挑戰不只來自揣摩角色的內心,還有聲音的極限。在與飾演妹妹朱家倩的韓國演員金仁馨共同演唱經典對唱曲〈還有一顆心可以碎〉時,張世珮坦言,一開始就感到極大的壓力。「她的技巧和爆發力其實是可以贏過我的,尤其是那段合唱高潮,剛好落在我最尷尬的換聲區。」
真聲到極限之後,必須轉為假聲,第一版演出她就是用這樣的唱法完成,但她對那個版本始終不滿意。「那時候我告訴自己:張世珮,妳要練。」
於是,她開始瘋狂練習,調整發聲、重組呼吸、拉升音域,練到整條街都聽得到她唱那段高音。面對難度高的歌曲,她靠著一己之力,一步步逼近目標,只為讓聲音撐得起角色情緒,並與對戲演員做情感抗衡。「我真的很感謝金仁馨的出現,她讓我知道自己還能再進步,還有東西可以突破。」話語中不只是感謝,還有職人挑戰自我極限的傲氣。
戲裡,朱家珍與朱家倩針鋒相對;戲外,兩人卻建立了深厚的默契。由於語言隔閡與文化差異,金仁馨一開始連叫她的名字都不敢,但為了演好一對鬥嘴又鬥氣的姊妹,張世珮主動拉近彼此距離,會下戲後約對方吃飯、逛街、聊天,培養真實的情感厚度。「我們戲裡要吵架,感情一定要夠真,吵起來才會好看。」她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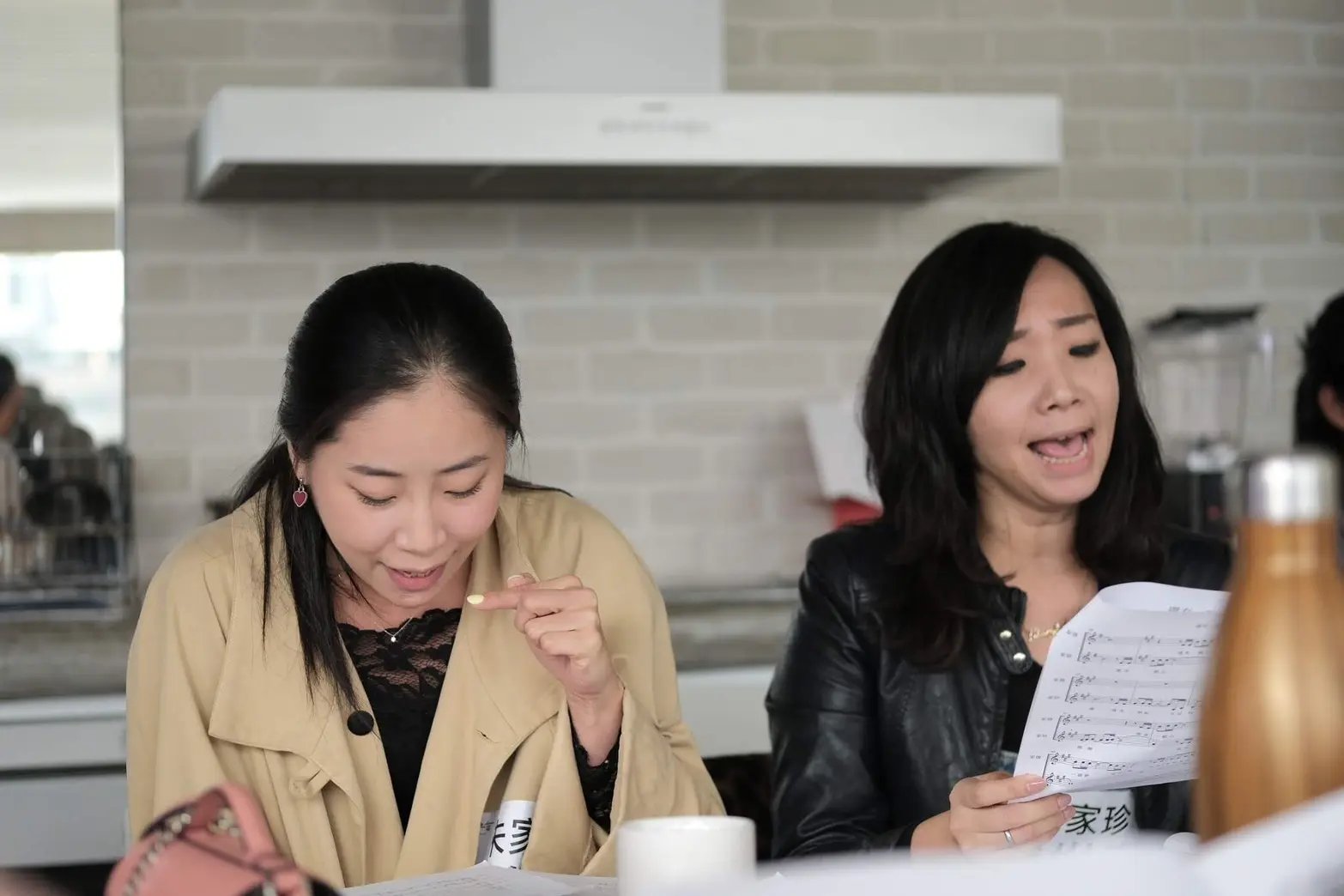
這一段演出,對她而言,不只是技巧與戲感的交戰,更是一場從外在到內在、從聲音到心境的蛻變歷程。她從最初的不理解、不熟悉,唱到某天真正「唱懂了」那首〈還有一顆心可以碎〉,不只是用技巧堆疊,而是她與朱家珍的情緒合而為一的展現。
中場休息:舞臺燈光暗下,是一位不肯放手的「超人母親」
舞臺上,張世珮總是全力以赴,卸下角色之後,她馬不停蹄地全力扮演另一個角色——母親。
「我是貪心的媽媽,想要全程參與女兒的成長過程。」張世珮想將戲演好,也想親自參與孩子成長的每一刻,絕不缺席。從女兒上小學那年開始,她每天清晨 5 點 50 分準時起床,幫孩子做早餐、送她們上學,接著利用空檔時間衝去排練、教課,再趕回家顧功課、陪吃飯,等女兒睡著了,才終於有時間練歌、背劇本,經常忙到凌晨 2 點,隔天再準時醒來,重複相同的忙碌日常。
她靠著強烈的母愛和意志力,奔走於劇場與家庭之間。這樣的堅持,從她第一次懷孕時就已經開始。那一年,她接演了《四月望雨》,飾演鄧雨賢的原配,而戲中角色也正巧是懷孕後期的設定。於是,她頂著真實的大肚子,全臺巡演。「我是邊排練邊孕吐,真的吐到很誇張。」即使身體不適,她也沒想過要暫離舞臺。

母親這個身分,對她來說不是責任,而是愛的延續。她記得小時候爸爸說過:「世界上最愛你的一定是爸爸媽媽和弟弟,除了我們三個沒有人更愛你。」這份從原生家庭延續下來的安全感與信任,也成了她愛女兒的方式——以朋友的姿態靠近、以原則的堅持守護。
下半場:當身體失速 用意志把自己拉回舞臺中央
挺著孕肚完成巡演、邊吐邊排練也從未缺席舞臺的張世珮,卻在疫情過後,遇上突發暈眩症,讓她的世界變得天旋地轉,「暈眩症剛發作的時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可能沒辦法再演出。」她雲淡風輕地提起,仍可讓人體會到她當時的心慌感同身受,「只要少了一個人,所有舞臺走位都要換,之後有遇過一個演員,演出前一天盲腸炎需要開刀,大家留下來加班,用一個晚上去排練新的走位。因為劇場就是『人』的地方。」深知劇場運作與緊密的她,最害怕的不是身體失控,而是讓整組人馬的心血付諸流水。
有一次在球劇場演出兒童劇,張世珮演出時暈眩症嚴重發作,休息時製作人直接宣布:「若是再發作,其他演員趕快把世珮帶下臺,直接停演。」張世珮聽到如雷轟頂,那一刻,她咬緊牙關召集其他演員說:「我一定撐得住,再糟糕也就是那樣了,絕對不能停!」靠著一股信念,她硬是完成了整場演出,像把自己釘在舞臺上。這次經驗,也讓她意識到,是時候調整節奏了,「如果以後不能上臺也沒關係,至少我還能唱歌、還能教學,還在音樂劇圈裡。」

事實上,在病症發作前,張世珮早已投入教學生涯,從演出空檔開始累積經驗,不知不覺這條教學之路已經走了十多年。過去在舞臺上,是為了自己表現、爭取掌聲;但當了老師後,她說:「我看到學生要上臺,比我自己上臺還緊張!」比起自己的發光發熱,張世珮更希望鎂光燈能好好落在學生身上。
「只要他們有一點點進步,我就會覺得超級開心。這個成就感,已經超過當年站在舞臺上的我了。」教學的角色,讓張世珮不只繼續唱、繼續說故事,也讓她以另一種節奏,繼續走在劇場路上。她不再只是撐著病痛上臺的演員,而是用豐富的音樂劇經驗,成為後輩眼中的引路人。
謝幕:那些劇場教會我的事 盼臺灣音樂劇走入日常
在劇場打滾多年的張世珮坦言:「臺灣的劇場還養不起音樂劇演員。」多數人仍需在演出之外兼職打工,才能支撐生活。即便現實不易,她依然對臺灣音樂劇的未來抱持樂觀。她觀察到,雖然產業尚未成熟,但已有越來越多的團隊願意投入到劇場中,也有學校設立相關訓練科系,各式劇種百花齊放,充滿各種可能性。
「只要有人來看戲,就會有收入;有收入,才能做更多的事。」她相信,音樂劇有一天能走進更多人的日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她積極投入教學,傾盡所學培養新一代表演者;下戲後,她不吝與觀眾簽名互動,拉近劇場與人們的距離,讓更多人感受劇場的魅力與溫度。

劇場裡千迴百轉的情節、汗水淋漓的排練,都如人生百態般豐富了張世珮的生命。「劇場對我來說是一個成長的地方。它給了我很多快樂,同時也帶來了不少挫折,但最重要的是,它教會我如何在跌倒後重新站起來。我真的很喜歡它。」回望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張世珮露出溫柔的笑容,緩緩訴說著。
劇場不僅教會她如何表演,更教會她如何生活。就算偶有迷失與跌跤,也能學會放慢腳步、調整節奏,重新與生命合拍。如同音樂劇的旋律,有高潮也有低谷,不變的是那顆熱愛舞臺,以及熱愛生活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