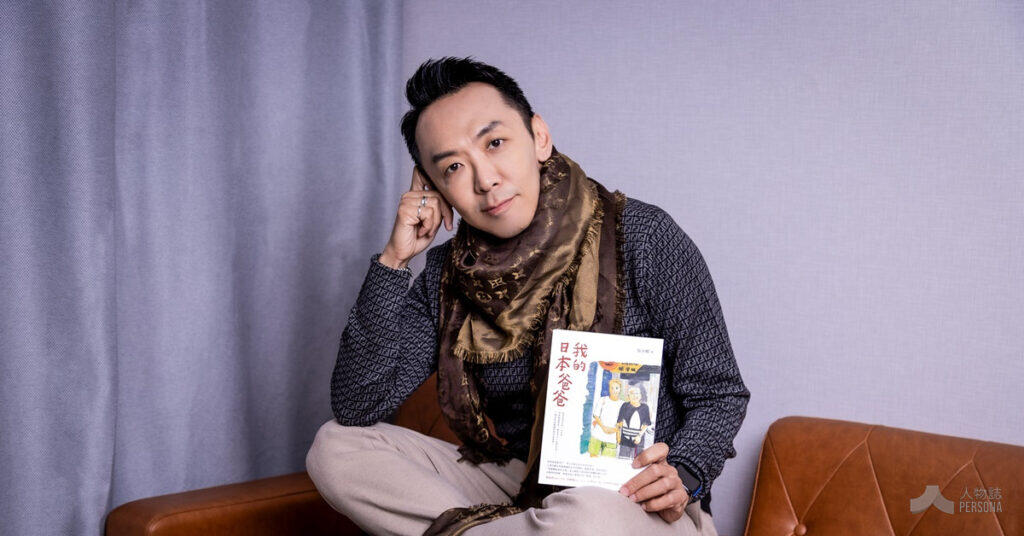用紙筆走進戰場的獨立記者——楊智強,走過緬甸政變的街頭、於泰緬邊境穿梭,也陪伴戰爭下的難民說出鮮少被記錄的創傷。他相信新聞不是單向的傳遞,而是一種陪伴與責任。在報導資源嚴重不足的地區,他帶著筆記本與錄音筆,穿越到國與國的邊境,替一群長期被忽視的群體說話。這是一段關於書寫、選擇與新聞意義的報導歷程。
從國際關係到新聞現場 理想如何變成如今的自我形狀
在泰緬邊境的一座小鎮美索(Mae Sot),楊智強面對著一群自緬甸逃難而出,情緒激動的羅興亞難民。儘管語言不通,他仍透過翻譯,一點一滴拼湊出他們支離破碎的生命故事。那一刻的他,既是旁觀者,卻也與他們一同陷入命運的漩渦中,試圖向外界傳遞真相。而難民在困境中仍不願放棄生存的努力,成為楊智強持續以筆記錄、報導的動力,不讓微弱的呼救聲被淹沒。
「我想當記者,是因為我想從下而上的角度,去理解這些事情為什麼發生。」當被問起為何要選擇記者這條路時,楊智強這麼回答。

從英國、韓國到緬甸邊境,他的腳步始終向世界邊緣靠近。大學就讀外文系的他,因為交換學生計畫前往英國,參加了一場由校方組織的烏干達慈善行動,那是他第一次直面第三世界的現實,也在心中種下對國際議題的關注。退伍後,楊智強參與僑務委員會的「萬馬奔騰-國際事務青年人才培訓計畫」,前往美國修讀兩個月的國際關係課程,正式開啟了對國際政治的初步理解。返臺後,因緣際會下獲得赴韓國大型 NGO(非政府組織)任職的機會,對此他特別提到:「在韓國 NGO 組織的工作經驗,深深影響了我未來的職業方向。」
原以為自己會成為一名外交官,但一次次走入現場的經驗,改變了他的方向。在軍旅中,他親身體會到體制的僵化;赴韓工作期間,見識到由下而上的在地能量,親眼看見長期被主流忽視的邊界風景。那段時間,他時常參與街頭抗爭,深刻感受到人民力量如何一步步推動改變。他說:「韓國的 NGO 有著草根性,每週至少會有兩、三場抗議活動,我幾乎都會跟著他們行動,也因此看見了與過去截然不同的視角。」
回到臺灣後,楊智強進入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讀書,一方面希望能深化對國際議題的理解,一方面也開始思索自己未來的角色。在這過程中,他發現許多學長姐選擇成為記者,實地採訪參與社會運動的群眾。與其在體制中成為一名研究員,不如親身走入現場,成為說出真實故事的人。楊智強確認了自己的生活目標:唯有紙筆與身體一同走進現場,才能真正靠近真相,理解這個世界。
身分的轉換與獨立性 選題自由的限制與甜蜜
加入主流媒體,是楊智強記者生涯的起點。他曾在報社、電視臺與《報導者》任職,擔任編譯和記者工作,也曾數度離開體制,以獨立記者的身分穿梭於各種報導現場。在體制內,他經歷編輯會議的拉鋸與選題的反覆潤飾,親見媒體如何在「速度」與「深度」之間做出艱難的取捨;而在體制外,他切身體會到選題自主權所帶來的珍貴自由,這對一名記者而言,意味著能忠實書寫自己真正關心的事。
體制內的經歷,讓他學會自我獨立、團隊合作與社會觀察的技巧。「我雖然在電視臺工作,2016 年特地請假,並自費飛到韓國報導朴槿惠彈劾案。那時現場全是電視臺的轉播設備,只有我一個人拿著自拍棒,用手機錄製現場報導,當時還有很多民眾好奇我到底在做什麼。」楊智強在《報導者》任職期間,參與過多次的跨國合作,與不同國家的記者一起進行跨境報導,這些經驗都讓他獲益良多。
然而,這也讓他逐漸意識到,自己真正在乎的,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他說:「在體制內,你可以把題目做到很好,而在體制外,你想報導什麼就報導什麼。這兩種沒有哪個比較好,只是看你想選擇哪一種。」
對楊智強而言,轉任為獨立記者的關鍵原因,是能自行決定「我要去哪裡、我要報導什麼、我要怎麼報導」。他清楚不受限制的報導自由度,意味著要放棄穩定的薪水與機構資源。

早在 2015 年,翁山蘇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在緬甸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時,楊智強就曾短暫離開電視臺,自費前往緬甸進行採訪。2023 年 5 月,他結束與《報導者》的合作,再度以獨立記者的身分出發,走入那些沒有發聲渠道的群體之中,記錄被遺忘的邊緣故事。
「成為一名自由的獨立記者,不是沒有老闆,而是你成了自己的老闆。」楊智強認為自由並不浪漫,反倒是一種重新建構記者與世界關係的方式,擁有選題的自主權,不再只是被動地報導,而能主動地選擇要報導什麼,讓他與每一篇作品之間都建立起更緊密、更真實的連結。
即使經常面臨資源有限的挑戰,他仍願意堅持下去。每當他想起那些曾經接受採訪、願意站出來、未曾放棄說出真相的受難者們,他就更加堅信,眼前的困難並不算什麼。他說:「記者不只是寫稿的人,而是對這個世界,還懷有某種不甘心的人。」
現場是無可取代的 他選擇走進戰爭、難民與沉默之地
楊智強的採訪足跡橫跨緬甸、泰國及各地難民營。他曾報導羅興亞難民的流亡處境,也記錄緬甸政變後反抗青年的聲音。談起每次的採訪,他坦言:「除了語言上的隔閡與翻譯的限制外,當我請難民或政治受害者再次回憶並講述他們的經歷時,我都會先對他們說聲不好意思。若是對方情緒太激動,我會選擇在旁默默陪伴,輕拍他們的背,低聲詢問是否想吃點東西。」
面對這些傷痕累累的生命,他時常反思,自己從事新聞工作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其實我沒什麼資格跟他們說加油。」他說,那些在現場悄悄累積的情緒重量,雖然未必能完整呈現在報導的字裡行間,卻是真實存在,具有難以忽視的重量,而這也成為楊智強持續走入新聞現場、書寫真相的力量來源。

「走入現場是很重要的。」他特別強調地說:「雖然說現代科技很發達,但如果記者沒有身處在現場,許多小細節、小動作是察覺不到的。」有時人們會笑說,現代的新聞媒體就像是個搬運工,但其實記者的本質不應該只是一面鏡子,更是一種存在於現場、理解並傳遞的中介。
對此,他說:「我認為媒體若要做長篇或深度的報導內容,『現場』本身的存在意義,是更重要,也是必要的!」
新聞是媒介 報導是行動
不是每一篇報導都會被看見,也不是每一次出發都有掌聲等著迎接你,即便如此,楊智強仍選擇走向鮮少被關注的弱勢群體。他表示:「有人認為,是觀眾造就了臺灣的媒體亂象;也有人認為,是媒體自己墮落了。這就像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新聞人本身就應該肩負起一定程度的擔當與使命感。」
他相信新聞不是短暫的職業選項,而是自我生命信念的實踐。「新聞對我來說,不只是一份工作,也是我生命中不會消失的存在。無論你是地方記者、平面記者,還是像我一樣的戰地記者,每一種角色都同等重要。」
2024 年,楊智強與幾位媒體夥伴共同創立了《邊境之眼》。這不是一個大型的新聞機構,而是一座沉穩但堅實的書寫基地。成員是一群來自臺灣、關心緬甸事務的文字與攝影記者。他們與緬甸流亡的媒體人合作,致力於以中文持續報導緬甸的局勢與故事。

《邊境之眼》不只是報導的延伸,更是自由記者以自己的步調深入議題、與讀者建立真實連結的所在。不再只是為了「新聞」而新聞,而是讓報導成為一種社會參與的方式——達成連結、對話與反思的起點。
新聞不只是高牆上的擴音器、理念的布道所,也是記者用身體的行動,與受訪者託付信任的無盡傾訴,所換來的一點點理解,與一絲絲希望。他說:「新聞對我來說是密不可分的存在,楊智強就等於記者。所以我生命結束的那天,記者這個身分才會死去。」
專訪結束時,我問他,接下來是否又要前往泰緬邊境採訪?他靦腆一笑,點頭說是。對他而言,獨立記者這份工作,早已成為如同呼吸般自然的存在。他總是背起行囊,一次又一次走向戰火與硝煙之地。在他心中,那些遠方的聲音,總需要有人帶回來,他是他們的眼與舌,是少數能為戰火下的人們傳遞影像與聲音的存在。